大禹治水,疏堵结合,奠定九州,其精神核心不仅是驯服洪水的智慧,更是凝聚人心、顺应自然规律的宏大叙事,千年后的今天,“水脉与心脉”的呼应愈发清晰:水利工程守护民生安全,生态治理修复河流生命,而大禹“公而忘私”的奉献精神与“科学疏导”的治理理念,亦在当代化身为协同发展、人水和谐的实践指南,它回响在南水北调的浩荡清波里,扎根于长江黄河的生态保护中,更流淌在一个民族赓续文明、与时偕行的精神血脉深处。
洪水滔天,浩浩怀山襄陵,四千年前,华夏先民在肆虐的洪水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助,正是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,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应运而生——大禹治水精神,这不仅是关于治水的技术智慧,更是一种深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,一种在时间长河中不断重塑与再生的精神力量。
大禹治水的核心在于从“堵”到“疏”的范式转换,面对滔滔洪水,其父鲧采用筑堤堵截之法,九年无功而返,禹则深刻认识到“水之性,行至曲必留退,满则推之,卑则趋之”的本质规律,转而开辟九川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,以疏导为主,顺应水性而治之,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智慧,在今日看来,恰与现代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,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、生态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时,大禹因势利导的智慧提醒我们:真正的治理不在于征服自然,而在于理解规律、顺应自然、和谐共生。
更为震撼的是大禹治水过程中展现的奉献精神。“劳身焦思,居外十三年,过家门不敢入”,这简短的记载背后是何等惊人的意志力与奉献精神,十三年间,他“薄衣食,卑宫室,陆行乘车,水行乘船,泥行乘橇,山行乘檋”,走遍华夏山川,足迹遍及黄河、淮河、长江流域,这种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并非无情,而是将个体情感升华为对天下苍生的大爱,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,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,这种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价值选择,提供了对抗“精致利己主义”的文化资源。
大禹治水还体现了实践出真知的科学精神,他并非坐在庙堂之上空谈治水方案,而是“左准绳,右规矩,载四时,以开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”,亲自勘测地形水势,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调整治水策略,这种尊重实践、躬身实干的作风,与当代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一脉相承,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常缺乏真知的时代,大禹的实践精神提醒我们:真知灼见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接触与不懈探索。
大禹治水精神在中华文明史上不断回响,都江堰“深淘滩,低作堰”的设计理念直接继承了大禹的治水智慧;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延续了疏通水道的思路;历代治理黄河的工程无不汲取大禹的经验,更深远的是,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治水本身,成为治国理政的隐喻——治国如治水,宜疏不宜堵,从唐代纳谏如流到当代改革开放,无不体现着这种疏导而非压制、顺应而非对抗的政治智慧。
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,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、疫情蔓延、社会分裂等全球性挑战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滔天洪水”?大禹治水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:面对复杂系统性问题,我们需要的是全局思维而非局部修补,是尊重规律而非盲目自信,是团结协作而非各自为政,是持之以恒而非急功近利。
大禹治水精神穿越四千年的时空,依然熠熠生辉,它告诉我们:真正的智慧在于顺应而非抗拒,真正的力量来自团结而非分裂,真正的成功需要坚持而非捷径,当我们在个人生活中遇到困境,在社会发展中面临挑战,在文明进程中遭遇危机时,回望大禹治水的智慧与勇气,或许能够找到那条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“疏导之道”,水脉即心脉,治水即治心——这便是大禹治水精神永恒的回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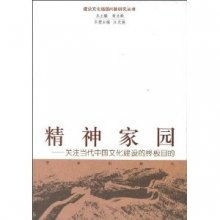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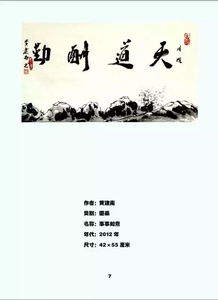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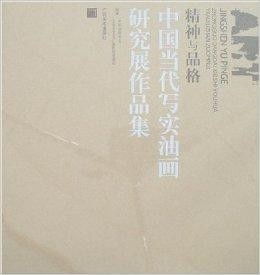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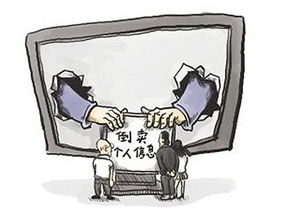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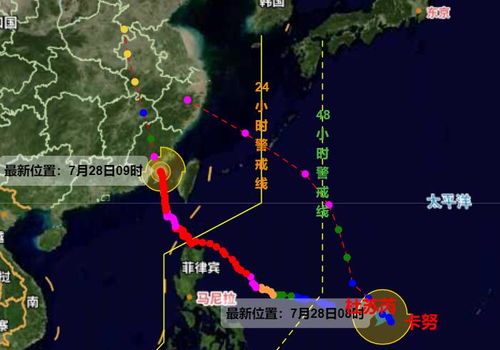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沪ICP备19017178号-1
沪ICP备19017178号-1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