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植芳先生一生坎坷,历经四次牢狱之灾,自比为“囚徒”,然而他始终以“星辰”自况,在漫长的黑暗与禁锢中,坚持以读书、思考、翻译和写作为武器,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,他的“不合时宜”,正在于拒绝向命运与时代强加的苦难屈服,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,这种于绝境中依然相信精神力量、并以之战胜现实苦难的信念,正是他真正的“精神胜利”——这不是逃避,而是以最顽强的姿态,完成了对荒谬命运的超越和对自我人格的捍卫。
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,贾植芳先生始终是一个“不合时宜”的存在,当众人高歌猛进时,他保持沉默;当集体陷入狂热,他冷眼旁观;当时代要求顺从,他选择质疑,这位四陷囹圄却九死不悔的思想者,用自己坎坷而壮阔的一生,诠释了何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风骨,贾植芳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功利主义时代的一记响亮耳光,他的价值正在于他的“不合时宜”。
贾植芳的“不合时宜”,首先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坚守上,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年代里,他拒绝成为“齿轮和螺丝钉”,坚持“思考是第一位的”,这种独立性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——前后四次入狱,长达二十余年的监禁与劳改,然而正是在这些极端环境中,贾植芳完成了对自我价值的最终确认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监狱是我思想的淬火场。”这种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能力,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“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之气。
贾植芳的“不合时宜”,还体现在他对启蒙理想的执着守望,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,他依然坚信知识的价值与真理的力量,在复旦大学教书期间,他反复告诫学生:“读书人要有骨头,不能随风倒。”这种对知识分子操守的强调,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,贾植芳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批判性距离,这种距离不是疏离,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介入,他的书房挂着一幅自题:“冷眼看热世”,这五个字道尽了他与时代保持张力关系的智慧。
在学术研究上,贾植芳同样走着一条“不合时宜”的道路,当学界热衷于宏大叙事时,他却专注于被忽视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;当众人追逐西方理论时,他却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的实证研究,这种不趋时、不媚俗的学术态度,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可替代的贡献,他主持编纂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等著作,至今仍是学者必备的工具书,贾植芳用他的学术实践告诉我们,真正的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,需要有一种“反时代”的勇气。
贾植芳的“不合时宜”,最终升华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,他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理论,而在于用生命践行了一种知识分子应有的存在方式,在普遍犬儒化的时代,他坚持理想而不堕虚空;在价值混乱的年代,他保持清醒而不陷孤傲;在物质至上的年代,他坚守精神而不落贫瘠,贾植芳让我们看到,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时代的“牛虻”,通过不断叮咬使社会保持清醒。
我们怀念贾植芳,不仅是怀念一个人,更是怀念一种正在消逝的精神传统,在一个越来越精致利己的时代,贾植芳的“不合时宜”恰如一剂解毒剂,提醒我们知识分子的本质使命——不是权力的附庸,不是市场的奴仆,而是真理的守望者和社会的良心,那些曾经被认为“不合时宜”的品质——独立、批判、坚守——恰恰构成了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价值。
贾植芳先生已经远去,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仍在叩击着我们的心灵,在这个容易随波逐流的时代,我们是否需要更多这样的“不合时宜”者?是否需要更多敢于说“不”的灵魂?答案不言而喻,贾植芳式的“不合时宜”,不是固执己见,而是对真理的忠诚;不是逃避现实,而是对理想的坚守,这种“不合时宜”,最终将成为照亮时代前行的星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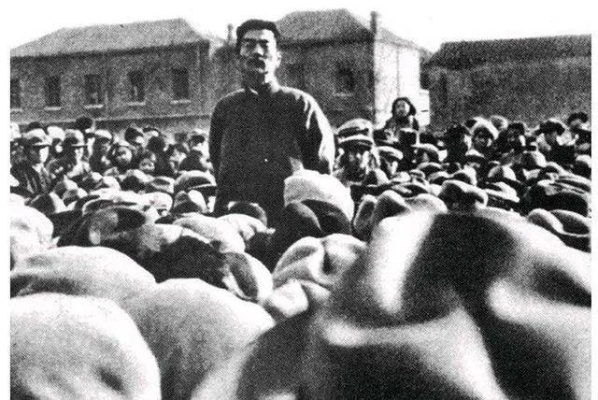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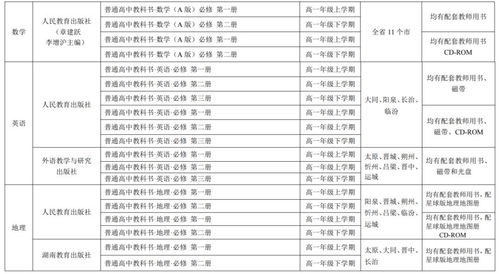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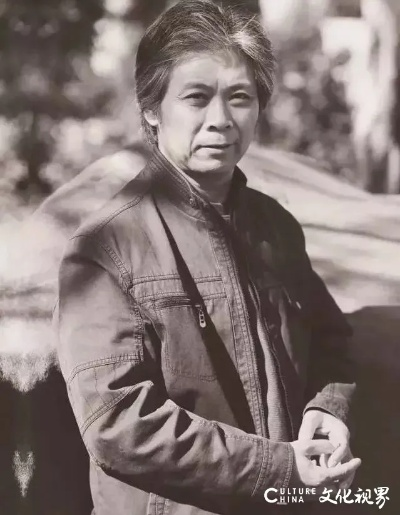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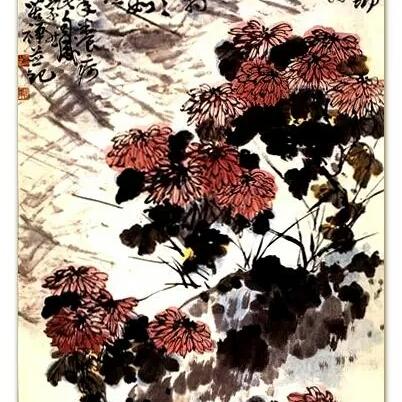



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沪ICP备19017178号-1
沪ICP备19017178号-1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